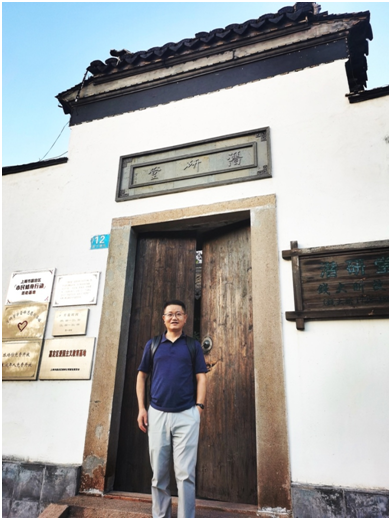
作者:李榮山
期刊🦘🤽♀️:《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摘要😗:文章認為🫘🫚,長期以來🧔🏻♂️,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深陷“非西方社會為什麽沒有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的韋伯式問題意識😞,進而波及韋伯與西方中心論的關系以及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系問題🔢,百年來難有定論🐦🔥🕝,錯失了基於中國文明主體的提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1)在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韋伯承接了歷史主義對特殊性的關註,對現代資本主義作了獨特界定,使得理論上西方以外不可能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2)在西方中心論問題上,沒有找準韋伯文明比較的標準📦☯️,容易陷入意識形態之爭,遮蔽了其文明比較中“和而不同”的可能性👏🏼;(3)在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系問題上👨🍼,沒有揭示出二者在理念型中相結合的機製🧑🏽🏭,難以把握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有必要立足中國文明自身重新發問🦹♀️,批判地檢討韋伯比較歷史社會學的得失,以講出中國道理。
韋伯的歷史比較方法有兩大核心特點🤟🏻:在概念形成上的“虛實相生”,在文明比較上的“和而不同”🦡。前者指韋伯的理念型方法是取歷史主義與新康德主義二者之長加以融合的產物👩🏻🎓,也是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融合的產物:使追求普遍性的“類概念”接受追求特殊性的發生學特性,轉變成理念型概念🤦🏼🧏🏽,成為構建歷史個體的分析性工具,這是歷史學與社會學在概念形成上相融合的關鍵✭。理念型概念“虛實相生”特點表現為👉🏽:一方面,概念是根據理念虛構的🙆♀️;另一方面🧑🏭,虛構的要件是具有實在性的歷史經驗。後者指韋伯利用理念型方法進行文明比較時,構造了二維比較坐標:一是“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二是“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世界圖像”規定了文明的走向👩🏻🦽➡️,“利益”推動文明按此方向前進🧛🏽♂️,二者各要件的相互組合共同確定了一個文明在歷史經驗中的具體軌跡📘。文明比較,實際上是去探尋二者各要件在諸文明中的具體組合形態。這套比較方法較為合理地處理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既能夠看出諸文明的普遍性🧑🏻🏫,又容易看出諸文明的特殊性,有利於揭示諸文明之間“和而不同”的格局。通過這樣的比較,韋伯不但把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呈現出來了👨🏻🦯,同時也把其他文明的獨特性呈現出來了🥺:如印度的根本特征是卡斯特製度🦼,猶太教的根本特征是內外有別的“賤民民族”性格🥶,傳統中國的根本特征則是氏族國家。
但韋伯未能完全從其他文明的內部視角出發為其構建“理念型”🧶👨🏿🏭,且過於強調特殊性🪺,故依然帶有文化本質主義的局限。文章采取中國文明的內部視角🈷️,從“世界圖像”和“利益”(或者說表達“利益”的組織製度)兩個層次粗略重構了中國文明“理念型”的一些關鍵要件🐈⬛🎩。從中國文明的內部視角來看✵,則這幅“世界圖像”並非韋伯筆下巫術的👨🏿🎓、儀式主義的和消極被動的,而是高度理性的、充滿情感的和積極主動的。拿這幅“世界圖像”和清教的“世界圖像”比較可知,二者有一個類似的實質性起點,即氏族關系🛐。只不過一個沿著氏族關系,一個打破氏族關系,向著不同的方向理性化為兩條不同的生活之道,正所謂和而不同🚶🏻。就利益層次(或者說表達“利益”的組織製度)而言,家產官僚製和封建製雖然是人類普遍存在的製度形態🔖,但在中國由於受倫理本位的世界圖像的影響🥪👱🏻♂️,又有種種特殊的表現👉,同樣體現了和而不同。
韋伯式比較歷史社會學構建的“世界圖像—利益”雙層模式內在蘊含著“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較理念。利益層次主要體現的是形式上的“和”, 世界圖像層次主要體現為實質上的“不同”🚣🏽,呈現出部分相似🧛♀️、整體相異的格局。這種視野有利於破除實證主義造就的虛假普遍主義,也有利於破除極端特殊主義的封閉性🧎,但“整體相異”依然落腳在特殊主義一端👩🏿✈️,特別強調各文明體在根子處的不同,依然帶有文化本質主義的特點,還只能達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要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上升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尚需在世界圖像之上的人性論層次(或者中國人所謂性與天道)尋找“和”的根基✮☁️,在這方面中國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有著特別的優長。文章結合費孝通晚年對文化自覺的反思來加以闡發:中國文明由於人性論上的優長,能夠開辟出一條“將心比心”的“禮”治之路,為世界貢獻一種真正“和而不同”的普遍主義🚣🏻,有助於再造文明間共識🚵🏻♂️,構建一個“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


